为何两只拥有生存智慧的八哥,成功避开村民的猎杀,却未留下后代?


“精”,在村庄的词库里是常用词,含义丰富。聪明,有能力,会办事,乃至于占便宜、不吃亏、鬼脑筋等,都可归之曰“精”,具体的指向要看语境。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清晰的语义,我理解,“生存智慧”这四字庶几近之。
“精”不仅能用于人,也同样能用于具有初步思维能力的动物身上,比如狗,家畜、飞禽。在村庄西边,风磐中学操场的一棵高高的法梧树上,栖息着两只八哥。这两只八哥形体同普通家鸽大小,白嘴,黄脚,全身羽毛乌黑透亮,雄八哥头顶上有一撮突起的冠状毛。它们在村庄已经“精”出了名。因此,也可以说,它们是两只具有生存智慧的八哥。
那时,猪肉价贵,还凭肉票定额供应,家禽早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。人们开始向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找下酒菜乃至改善伙食。村子依山傍水,林密,鸟多。村子里有几个“神射手”,玩弹弓不说百步穿杨,也基本是弹无虚发。村庄四周林子里的鸟,除了麻雀、黄鹂(个太小,肉太少),斑鸠、喜鹊、黄嘴鸦之类的都打得差不多了。这两只八哥早就被瞄上了,但始终没有一个得手,其中余大、刘二最有代表性。

余大是铁匠老余家的老大,神射手中公认排名第一。弹弓虽不等同于弓箭,但同样需要力量和精准度。余大因为天天抡铁锤的缘故,练就了一身好臂力和好眼力。大家故意把他叫成“驴大”,大概是有一身驴劲的意思。我经常遇见驴大用巴茅草或柳条穿着一串斑鸠或喜鹊,弹弓别在大裤衩上,从村后树林里的小路晃荡回来。驴大想过很多办法对付这两只八哥,但一直没有奏效。比如,这两只八哥觅食饱了喜欢蹲在树下的大教室屋脊上晒太阳,这时候没有遮蔽物,八哥全身暴露面积最大,是射杀的最佳位置。驴大多次提前躲匿在大教室墙边的阴影处,绕着墙根慢慢挪到八哥背面的矮屋。驴大调整好身姿,屏住呼吸,头刚探出来,八哥似乎闻到了空气中传来的危险的信息,警觉地蹲下身子,昂起了头。雄八哥头顶上的冠状毛一根根竖起来。驴大刚刚举起弹弓,橡皮筋还没来得及拉开,两只八哥一挫身,一振翅,倏地掠入树丛中。几个平时屡试不爽的方法一个不灵,驴大有些恼羞成怒。最后,驴大决定上树,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?”其实手脚再轻,上树也有动静,不可能不惊动八哥。驴大是想打烂它们的老巢泄愤。八哥的巢筑在树顶一棵斜着的枝桠上,在地上只能隐约看到巢的轮廓。驴大将弹弓别在腰上,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,上树了。这棵法梧树从树干分出树杈,大约分为四层。驴大上到第二层,抬了抬头,树叶太密,看不清。上到第三层,八哥巢看得清清楚楚了。驴大骑在斜伸出来的横桠上,抽出弹弓,拉紧皮筋,对准八哥巢。这时,两只八哥不知从哪飞出来的,鸣叫着,一前一后俯冲着飞下,雄八哥啄向驴大的脸,雌八哥啄向驴大的胳膊。驴大猝不及防,摔了下去。幸亏第二层枝桠挡了一下,坠下的过程中驴大又下意识地拽了一把枝桠,还好,摔得不算重。但就这样,驴大胳膊还是摔骨折了。
伤筋动骨一百天。驴大到医院打了石膏,在家里歇了三个月。以后再见到驴大,驴大的精气神像是散了,整个人就蔫了。

刘二在神射手中的排名不可考了,但肯定属于第一梯队,和驴大的射技不分轩轾。吸取了驴大的教训,刘二认为这两只八哥不可力敌,但能智取。刘二说对高智商的鸟要用高智商的办法,这叫“以毒攻毒”。刘二认为八哥落在屋脊上时仍然是最佳射击位置,这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刘二在离大教室十来米的地方搭了一座简易草棚,搭好后五天不去管它,先让两只八哥适应,打消它们的警觉性。五天后刘二在棚子前面挖了一个碗口大的射击孔,上沿搭了几根稻草。刘二弓在棚子里瞄了一下,弹弓、射击孔、屋脊正好处在一条直线。挖好后刘二也不着急,三天没管窝棚。到了第十天,刘二觉得差不多了,时机成熟了。一大早刘二就守候在窝棚里,眼睛紧紧盯着屋脊,手上汗涔涔的,弹弓柄滑溜溜的。这天,两只八哥一共飞来屋脊五次。每次,刘二都觉得自己很有机会。但是每每刘二校准角度、拉紧皮筋、将发未发之际,两只八哥仍是一挫身,一振翅—飞了。
刘二在窝棚里守了三天,但每天都在重演第一天的一幕。最多的一天,两只八哥飞来大教室的屋脊有七八次。第四天,刘二捱不住了。找了个没人的傍晚,刘二悄悄把窝棚给拆了。过几天见到人,刘二总是讪讪的,满脸“出师未捷”的神情。
这以后村里人见到驴大、刘二,总是故意问问:“打着了?打着了吧?”驴大苦笑笑,啥也不说,扭头就走。刘二则摇摇头,叹口气说:“精,精!”以前见面打招呼,村里人总说“吃过了?吃过了”。现在,“打着了?打着了(“打”读重音,后两个字近似于儿化音,但第二个“了”读音稍重)”用久了,代替“吃过了?吃过了”成为村庄的日常问候语。
对于即将和已经临近的危险,两只八哥具有无与伦比的听觉、嗅觉和洞察力。而我以为,两只八哥的生存智慧,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。
我曾无数次近距离观察、接触过两只八哥。

离我家不远的地方、推开窗户就能看到一口井,两只八哥经常飞来井边喝水、洗澡。雌八哥喜欢站在井边麻石的水窝子里,一边用嘴叼水梳理翅膀,一边扑拉着翅膀,抖得水珠四溅。雄八哥蹲在井沿,蹦两步,停停,东望望西望望,再蹦两步。我想:它一定是在担当警戒的角色。我经常放下手中的作业,跑到井边,一看就是半天。我去了,两只八哥并不飞开,离我只有一两尺,似乎一伸手就能捉到。有时候,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过去,想将它们托在手心,再仔细看看它们白色的喙,黄色的脚,圆圆的晶亮亮的眼睛,眼睛四周一圈黄色的胶质状眼眶。还有雄八哥头上的一撮冠状毛,我数了数,一共有九根,多想用手摸一下。可当我将手伸过去的时候,雄八哥轻轻蹦了两步,停下,再蹦两步,离我还是一两尺,歪着脑袋,用一只亮晶晶的眼睛狡黠地看着我。似乎是在说:想捉我吗?
它们的羽毛多么好看啊,乌黑乌黑,和白色的喙、黄色的脚配比得那么和谐。它们在天空中飞翔的时候,姿态是那样优美。我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、修饰。直到上初中学到高尔基的《海燕》这一课,我才恍然大悟:对啊,可不就是“一道黑色的闪电”!我曾用稚嫩的笔这样写道:“它们一振翅,在天空中划过一道黑色的闪电,一敛翅掠入林中,又像倏然消逝的一缕夜色。”
两只八哥的鸣声很特别(雄八哥高亢一点,雌八哥略为婉转一点):
“八个九~八个九”(“个”音很轻,一带而过,“九”最重,音同“就”)
一年四季,它们以或远或近的鸣声见证、宣告自己的存在。后来我来到县城、都市,见到过人们囚在笼子里的宠物八哥,也在城郊的山林里见过野生八哥,但它们的鸣声都是单音节的,类似于啄木鸟或喜鹊的“喳—喳”或“嘎—嘎”。夏天,是鸟叫虫鸣的盛季。蚕永远是在知了知了地聒噪,油葫芦的声音悠长而拖曳着一些尾音,纺织娘在傍晚叫起来,像开了一支高音喇叭。但我总能从无数重叠着的虫鸣鸟叫中辨别出这两只八哥的鸣声,雄八哥的高亢,雌八哥的婉转,它们或远或近或高亢或婉转的鸣声像是穿透岁月而来,来到村庄,这给了童年和少年的我多少欢乐与慰藉。
然而一直让我纳闷不解的是,两只八哥为什么没有繁衍后代。我查过《十万个为什么》:八哥一年孵巢一次,一次一般孵化两枚蛋。八、九年时间,也该有十六、七只小八哥,小八哥还能生小小八哥。照理,小八哥们必定继承了这两只八哥的基因。当一群八哥“八个九~~八个九”地鸣叫起来,场面该是多么壮观。然而一年又一年,我所见到的还是这两只八哥。它们或许已经生下了小八哥,移居去了别的村庄和树林?但是我在四周的邻村的屋顶和树林见到过八哥,它们的鸣声都是单音节的“喳—喳”或“嘎—嘎”,单调而暗哑,没有一个发出“八个九~~八个九”的鸣声,这使我坚定地认为它们必定不是这两只八哥的后代。
或者,对这两只八哥而言,我们这座村庄的生存环境太过险恶,缺乏小八哥成长所需要的宽容和呵护,它们只好过起了现在所谓的“丁克”家庭的生活?

这个疑惑我曾经问过母亲。母亲愣怔了半天,最后忍俊不禁地笑了。她大概对这两只八哥是否具有这样的生存智慧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王小波有一篇散文名作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。我以为,那是一只“虚拟”的猪,于荒诞中凸显“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”的象征意义。而我的这两只八哥,完全是写实的。我自然不会贬低它们,也丝毫没有刻意美化、拔高他们。母亲曾以两只八哥为例对我进行人生启蒙:“做人要精一点,像那两只八哥。一年过了一年,还在那儿飞、吃食。”我至今学不会“精”,但我喜欢这两只八哥的“精”。否则,它们的鸣声就不会陪伴我的童年、少年那么多年。有时候我想:假如人们将所能想到的卑劣手段使出来,下毒、拉网、砍掉那棵法梧树以及周边山林、毁坏它们的栖息地......它们的生存智慧还能抵挡那命定的厄运和劫难吗?
而在我的想象里,那“八个九~~八个九”的嘹亮的鸣声,满含生命的自由、愉悦和对某些心怀叵测的人的不屑,至今响彻整座村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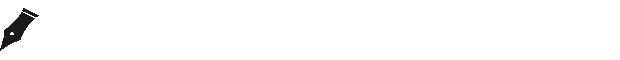

周海,70后,安徽省枞阳县人,写散文,偶尔写诗。大学期间开始写作,著有散文集《风吹来的地方》。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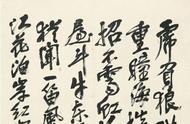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7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7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