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诗的奥秘」探究约翰·济慈对真正诗歌的定义

大地的诗歌永不消亡:
当炎炎烈日把百鸟晒晕,
藏进凉爽的树间,有一种声音
却在新割草场旁的篱笆间飘荡。
那是蝈蝈的嗓音,它带头歌唱
在奢华的夏日,它的欢欣
永无止期;当它兴头已尽
就去怡人的草叶下安歇。
大地的诗歌永不终止:
在孤独的冬夜,当严霜
冻出一片寂静,从炉边
响起蟋蟀尖声的吟唱,而炉火渐暖,
那睡意朦胧的人恍惚又听见,
是蝈蝈歌唱在绿草茸茸的山间。

世界诗坛不乏早夭的天才诗人,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约翰·济慈(1795—1821)是其中突出的一个。因为早夭,济慈投身诗歌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年。这十年却是他烟花绚烂的十年,也是他为自己赢得诗名不朽的十年。在济慈一系列已成经典的诗歌中,这首《蝈蝈和蟋蟀》特别令人难忘。该诗问世于1816年12月30日夜间,其时,年仅二十一岁的济慈与友人亨特、克拉克在火炉边取暖。谈话间听到炉边有蟋蟀出声,亨特诗性骤起,提议以《蝈蝈和蟋蟀》为题,他和济慈各写一首十四行,由克拉克计时,看谁先完稿,结果,才思敏捷的济慈率先交出这首臻于完美的名篇。这首诗的确给人浑然一体之感。身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五巨子之一(另四位分别是华兹华斯、柯尔律治、拜伦、雪莱),这首十四行既像济慈其他名篇如《夜莺颂》《秋颂》一样,不乏浓烈的浪漫色彩,同时又具有超越浪漫的非凡力量。这种力量来自人对世界的某种真理性认识。纵观古今中外的顶尖诗歌,无不显示出这一认识。

界定什么是顶尖诗歌,历来见仁见智,最起码有两类诗歌格外令人瞩目,一类是以新奇的意象夺人眼球,一类则以揭示世界的某种本质震动心灵。以意象新奇取胜的,更多来源于诗人的敏感和天赋;以揭示世界本质取胜的,则取决于诗人对生活的认识是否到达诗歌本身所要求的高度。后一类诗歌的成品看似平常,实则对诗人的考验更为巨大。以济慈这首十四行为例,诗篇起句“大地的诗歌永不消亡”颇像哲理,说它像哲理,是因为哲理和诗歌有着无限接近而又决不会重叠的空间。因此,在该诗起句里,我们与其说济慈表现出哲理,不如说他一步到位地提炼出大地的本来属性。而且,在这行诗中,济慈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也和盘托出——诗歌并非来自诗人的冥思苦想,而是来自大地。这种感受与认识并非济慈第一个有此强烈意识,但他是第一个在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坚决和果断的诗人。在今天,我们并不陌生一代代诗歌大师的反复告诫,诗歌的最佳表达方式是使用陈述句。陈述即肯定。将某种感受肯定地说出,继而让每一位读者接受这一肯定并非易事。诗人自身缺乏力量的话,根本做不到。济慈这行奇峰突起的起句惊人,就在于他毫不拖泥带水,而是直捣核心,揭示出人对大地或大自然的终极认识。

作为诗歌读者,我们容易体会,说一个人内心充满诗意,其实是说他面对事物之时,有一种叫“诗意”的感受投射到他的面对之上。对人来说,除了大地,几乎没有第二种更为真实的面对。因为人居于大地,生活居于大地,万物居于大地。二十世纪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也在他的一首诗中直言不讳地写道,“一切来自大地,一切又归于大地”(见米沃什《歌》,林洪亮译)。两位诗人异曲同工,想说的不过是人最终如何认识大地。
在济慈眼里,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诗歌元素。大地不会消亡,所以大地上的诗歌不会消亡。这是济慈极为坚定的内心认识,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诗歌观点——如果说诗歌充满大地不容否定,那么一只微不足道的蝈蝈和蟋蟀,也是大地上的诗歌组成部分。更重要的是,诗歌的本质属于歌唱,蝈蝈与蟋蟀的声音也会是歌唱的一部分,所以在这首诗中,没有哪个读者会觉得蝈蝈与蟋蟀的声音不值得人去重视。唯有重视大地上的每一种声音,才称得上是重视诗歌的每一种声音。

声音如何表现?这是济慈在起句之后的呈现。我们看到的烈日、树间、草场、篱笆等事物,蝈蝈在这些事物中亮出嗓音。它们并非诗人的想象,而是来自诗人的生活体验。当济慈将体验转换成动人心弦的诗句,我们不能说它是作者的浪漫情怀所致,恰恰是诗人的白描展现出最自然、也最强大的力量所致。济慈敢于使用白描,就在于他知道,诗歌来自大地,诗歌就决不需要任何修饰,诗人要做的,无非是将大地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表现出来。当济慈在该诗第三段以对应手法写下“大地的诗歌永不终止”时,我们能够感受,正是有“永不消亡”的前提,才会有“永不终止”的继续。更需强调的是,一连两个“永不”,看似是诗人在诉说信仰,实则是大地与生活给予了济慈深切的感受,所以,这里的信仰与其说是济慈抱有的信仰,不如说是大地本身蕴含的自我信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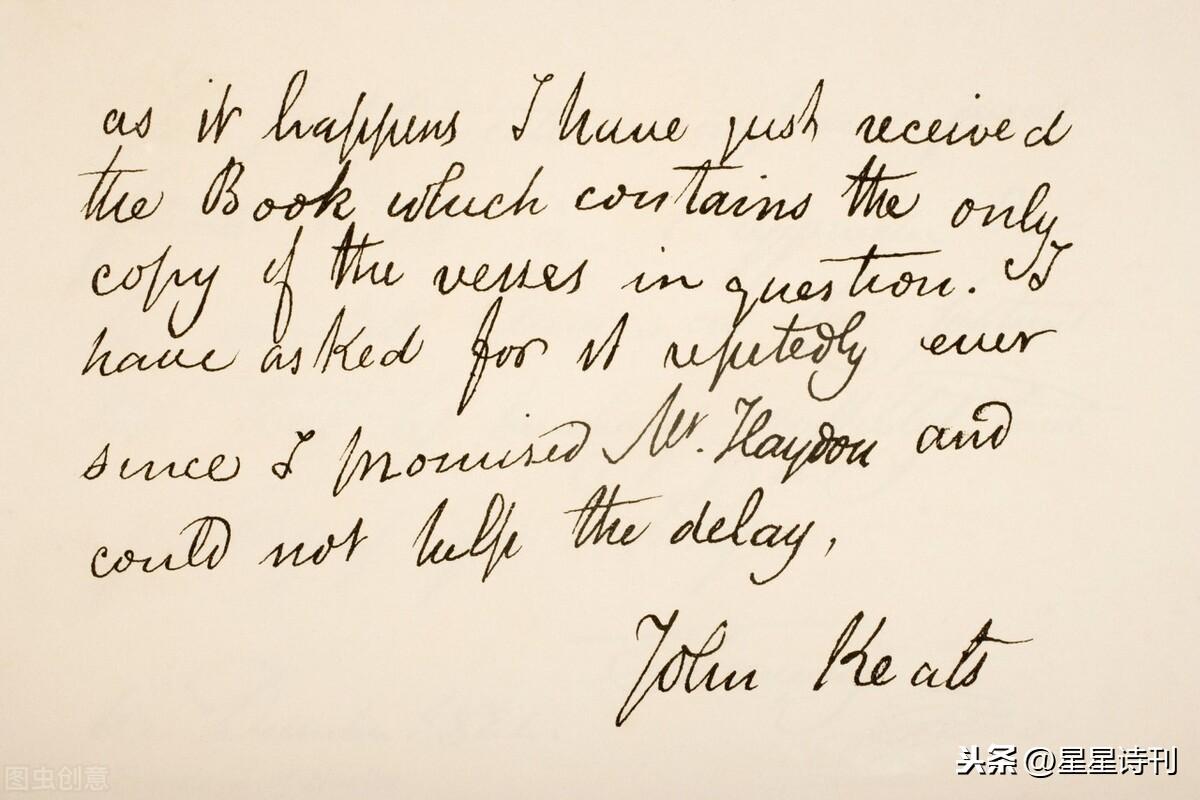
济慈这首短诗能成名篇,不仅仅是它在短短十四行内,做到细节上的真实和丰富,还在场景及季节的转换上,使诗的整体具有极开阔的视野,更重要的是,济慈借助蝈蝈与蟋蟀两个简单意象,为读者揭示了诗歌最本质的一面。放在今天来读,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大魅力。这魅力不是来自济慈,而是来自诗歌本身。无所谓古典与现代,步入永恒的诗歌无不具有时读时新的阅读张力。彼时的济慈年纪虽轻,已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大师笔触。诗歌本身的厚重感和语言的自如感在这首诗中水乳交融。
我们稍加留意,还能清楚地看到,全诗未着一个“我”字。这种诗人的自我退场,不仅在浪漫主义诗歌中,即便在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极为罕见。济慈选择退场,不是因为表达主题所限,而是他面对诗歌和大地之时,已觉察到人的渺小。诗歌会选择人来表现,却从来不会选择人成为诗歌本身。成为诗歌本身的,只可能是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。通过这首诗,我们能有把握地说,济慈几乎领先现代近两个世纪,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。人只是万物的记录者和礼赞者,所以,济慈这首诗是一首率先垂范的大地之诗,也是一首万物之诗。当人真切领悟到什么是大地和万物,也才会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诗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7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7号